微信扫码立即登录

《世界人居服务使用协议》和《世界人居用户隐私条款》
世界设计之都|创意城市网络:迟到的新城市主义范式
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设计之都”
2022-10-26阅读:4152发布:人居要闻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825期4版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 李鹏飞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源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004年便已成立的“创意城市网络”(UCCN)。“创意城市”(creative cities)并非一个空洞的城市设计行话。它作为一个设计原则和愿景是在20世纪末才在城市研究领域形成的新共识,是一个迟到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范式。

上海城市景观配图 (与正文无关)
新城市主义挑战的是在20世纪城市设计和城市更新中饱受诟病的极端城市主义。极端城市主义不完全是Louis Wirth在其1938年的经典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所描绘的、以芝加哥城市生态为原型的城市主义,而是在二战后被各国——以北美和巴西为甚——大力仿效的柯布西耶式的城市主义。柯布西耶式的极端城市主义全面改造了二战后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形态:商业、工业、居住、休闲功能的清晰分隔使城市变成了一架巨型的规划机器,而郊区化的全面推进又极大地剥夺了城市的居住空间。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极端城市主义铺展的过程中,街巷原有的商业和生活功能被其单一的交通功能取代:曾经可供漫步、可供邻里甚至陌生人社交的街巷变成了驱车前往居所和购物中心的道路,即可居街巷蜕变为交通线路。真正摒弃极端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原则要到20世纪后期了。而彼时的城市已然是被极端城市主义强力改造(破坏)过的城市。
上述对20世纪北美城市形态演化的简单概括为更好地理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提供了一个背景性的比较框架。一方面,上海的城市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了这个在战后被普遍推行的极端城市主义模式,城市空间形态在极大程度上被“封冻”了。另一方面,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高速城市化期间重拾起一种被改造过的极端城市主义,一种含有新城市主义元素的城市空间模式:商业、工业、居住、休闲功能的分隔是在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无论是在行政功能意义上还是在空间文化意义上,大规模的郊区扩张并没有把郊区从城市剥离;被大规模拆迁的原市中心街巷的确遭遇了极端城市主义开发模式的破坏,但大片保留下来的街巷在21世纪20年代仍然成为上海城市活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文化资源。
街巷的复兴与新城市主义 如果说20世纪中叶极端城市主义的推进带来了街巷的消逝/衰落,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新城市主义倡导的正是街巷的复兴。由于上海重拾极端城市主义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的城市空间改造和扩张中避免了两个重大失误。其一,上海原市中心区域只建造了三条高架路(延安高架路、南北高架路、内环高架路)。这种对城市内城的空间改造虽然是极端城市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把人居街巷变成机动车道路,但上海避免了用高架路撕裂城市生活空间的失误。其二,上海原市中心区域的延安高架路以南、西内环高架路以东、肇嘉浜路以北、南北高架路以西的大片城市街巷得以保留。这种对城市内城空间的大面积保留汲取了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它们也是Jane Jacobs在20世纪60年代就竭力倡导的原则:宜居的小街区、混合功能的建筑、对行人友好和公共交通主导的街道、小生意发达的街市。正是这种街巷的物质性存在,上海避免了北美诸多城市内城的消亡和中国诸多城市“千城一面”的失误。
城市空间文化 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新城市主义设计原则是对20世纪上中期以来极端城市主义的修正。从更广义的社会理论的脉络来说,它是对19世纪以来的过于乐观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修正。如果说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过于强调了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以创造出一个更先进、更美好的未来),那极端城市主义则过于强调了自上而下的规划对城市的改造(以创造出一个更先进、更美好的城市)。但城市和人一样,它不仅仅是一个机器,还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充满了由内向外的、自下而上的生长潜能。上海内城被保留的大片由小街巷构成的空间正是上海这个有机体的核心部分:它是行人友好的、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也是混合功能的、小生意发达的。当上海的居民(甚至外来的游客)厌倦了近郊和远郊同质的封闭式小区和大型购物中心时,他们会重新发现上海内城的异质和鲜活。他们甚至也会重思空间背后的文化脉络和社会理论——空间是如何形成的?它为了谁?
这种发现和重思既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也是人们共同打造更可持续的未来空间和未来生活的前提。只有在此种文化自觉之上,“创意城市”才能从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变成现实的城市形态;也只有在此文化自觉之上,上海的“设计之都”建设才可能真正引领21世纪全球城市形态的新范式。
《社会科学报》总第1825期4版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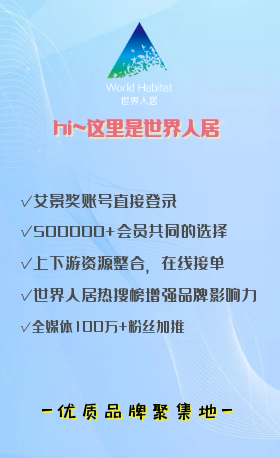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5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569号
评论
全部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