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详情
项目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的阳坡村,这也是陈富平先生的老家。在创立了桃园集团后,他一心想着如何能回馈家乡,重新振兴阳坡村。2020 年,他认识了隐居乡里的陈长春,俩人一拍即合,桃园集团出资建造,隐居乡里策划运营。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县城里工作,平时也都住在县城的住宅小区,村中的很多房子常年没人居住,破败不堪。桃园集团说服了一些村民将他们村中不住的宅基地交出,并在不远的山坡上建造了新的回迁房作为补偿。
其实前前后后设计的院子有十几处,但很多院子在设计或建造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无法继续,这样的情况在乡村改造的过程中非常常见,最终落地完成的一期项目可用院落一共八处,都是在原有的宅基地范围原址原建,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群落关系也基本保持了原有村落的肌理脉络。

鸟瞰图
隐居乡里以差异化乡村运营模式深耕民宿领域,核心围绕"在地之美"理念构建独特产品逻辑。通过极简设计将建筑自然融入乡土环境,引导游客聚焦真实乡村景观,同时保障居住舒适度。区别于单纯形态改造,更注重建立可持续"造血机制"——已成功改造的300余个院落验证了其运营前置策略:在设计阶段即植入标准化空间单元与营销需求,通过产品模块组合实现个性化院落的快速复制,有效压缩30%前期成本与50%决策周期。这种"非标产品标准化"模式不仅降低资金投入,更能规避乡村项目常见的开发周期风险,形成可复制的良性运营闭环。
隐居乡里最为人知的产品是利用废弃农宅改造而成的独立院落度假产品,与之对应的是经过培训的当地大姐提供的一对一的管家服务。经过多年的探索,住宿部分全部设置成独立小院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服务动线分散,运营成本高企; 另外这样的模式也使得项目往往出房量不多,与之对应的单房投资额过高,如果想要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后续的营销及运营都会背负很大的压力。真正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既要顾及原有的乡村生态,也需考量商业回报,成功的乡建项目都是二者间完美的平衡。
基于这样的思考,隐居乡里在这个项目中将住宿业态分成两个部分,多个独立小院继承了隐居乡里的品牌基因,也使得项目在体量及形态上都更容易融入原有的乡村环境。另外一处独立的小客栈则不仅仅是满足了市场上不同的住宿需求,也在一期场地收储有限的情况下相对增加了出房量,集约的服务模式也适当减少了运营成本。配合着住宿业态,项目一期开业时设置了一些公共服务配套,包括咖啡厅,餐厅,多功能厅,小卖部和教室工坊,这些功能空间可以在项目初期缺乏流量保证的时候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运营条件,等到项目运转成熟,流量逐渐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根据情况适当引进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公共业态或是引进一些成熟的内容运营商。

总平面图
在改造设计策略上,隐居乡里一贯采取的都是尽可能的少干预,尽量不做不必要的设计。我们一直认为乡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原本就真实存在的自然及人文生态环境,创造所谓的网红建筑既不是建筑师的义务,也不应成为建筑师的目标。
隐居乡里在乡村建造的目的只有两点,一是在满足运营功能需要的前提下为入住的客人提供足够的舒适度,二是通过建筑帮助客人更好的去发现乡村中原本就存在的美好。在此基础上,建筑师最大的责任是协调关系和控制成本。类似于乡村中传统的建造过程,我们的设计基本上是先根据成本以及当地的现有条件确定一个建造单元,之后再把这个单元去根据不同的场地进行组合复制。考虑到场地中现有民居的形态,确定了跨度2.6 米的窑孔作为住宿部分的基本空间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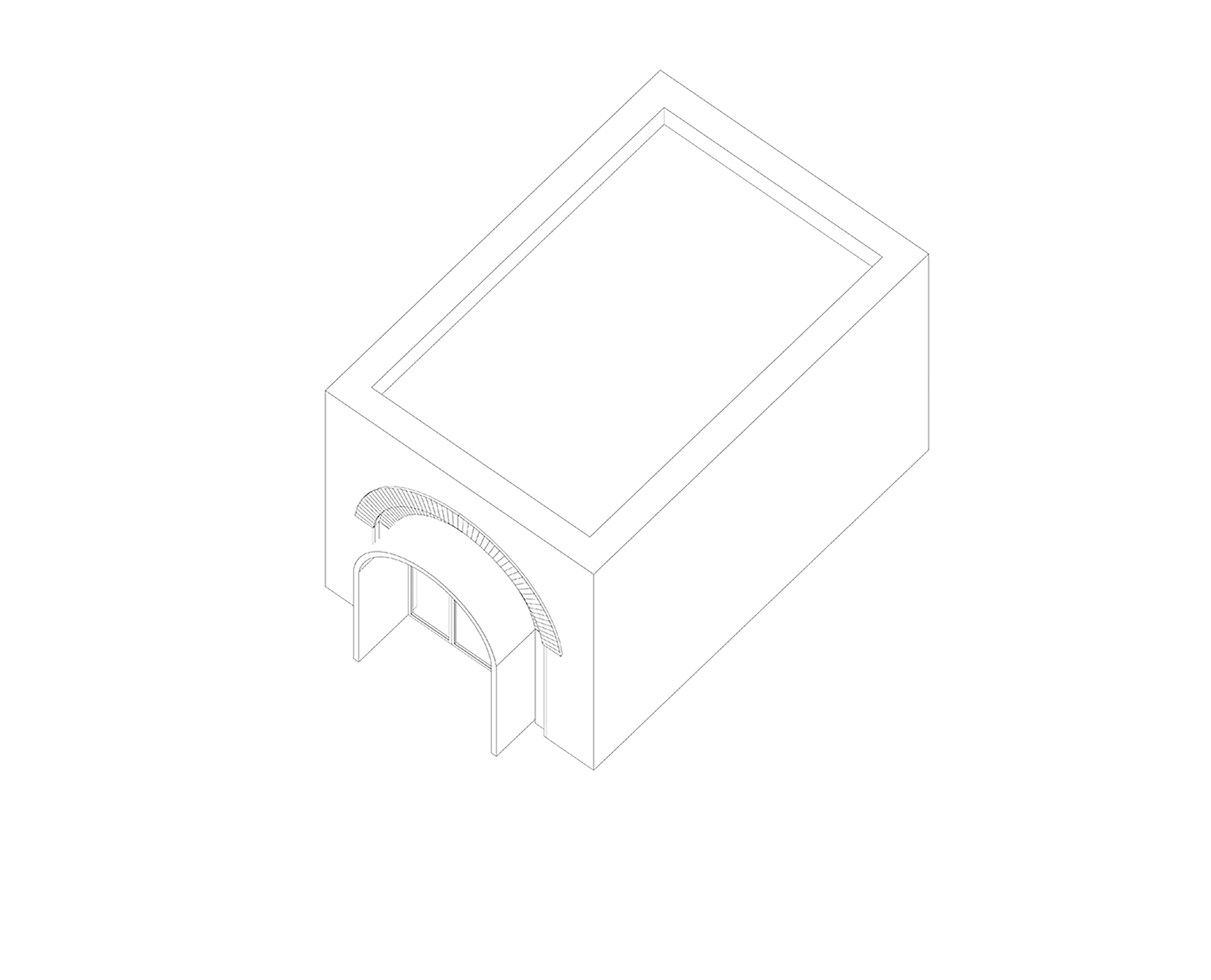
跨度2.6 米的窑孔作为住宿部分的基本空间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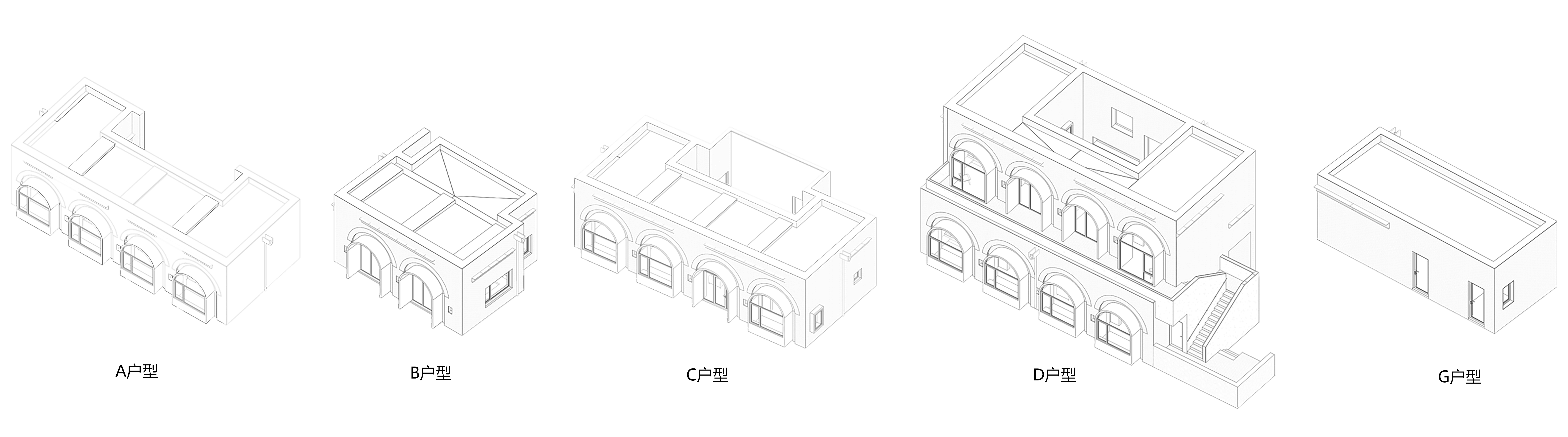
将窑孔组合成不同的基本户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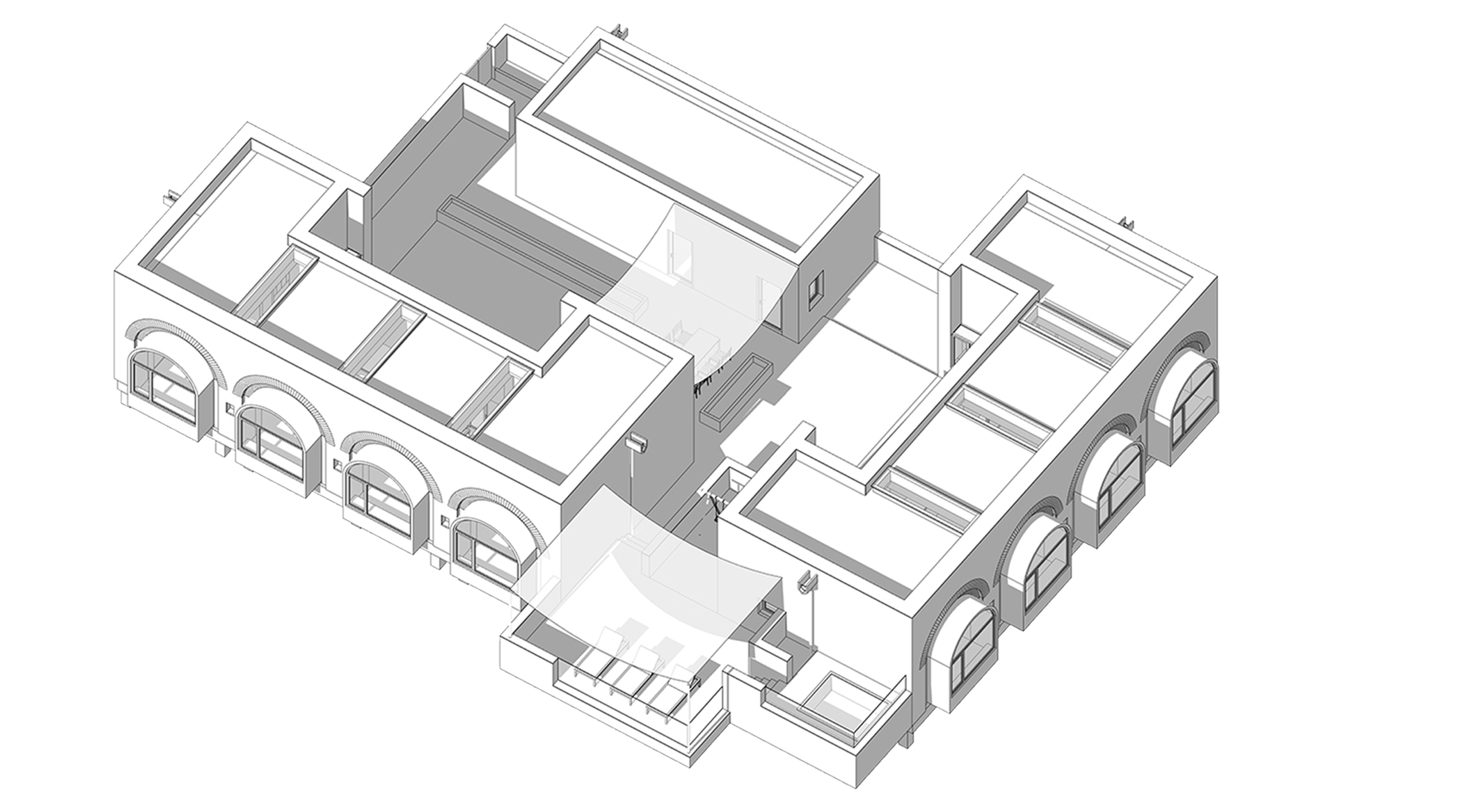
对户型进行组合复制
由于空间组合相对模块化,结构最初设想是钢结构,因为可以在现场快速组装搭建,从而尽量避免乡村施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后来了解到甲方自己有水泥厂,除了接待中心需要大跨空间采用了钢结构,其他住宿院落都改成了混凝土框架结构,这也体现出了隐居乡里在处理乡村问题时实事求是的态度。
最高处的场地面积最大,道路通达性也最好,我们就将项目中面积最大的接待中心设置在了这里。类似于希腊的雅典卫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项目场地,同时也能被村里的其他院落从远处仰视,在满足项目接待以及各种公共使用功能的同时,也自然成为了整个项目的精神堡垒。

接待中心北侧外观
接待中心的场地入口在东北角,U 型建筑体量所形成的甬道将人引致中心位置的帆棚下方(灰空间)。在这里,是原有场地中唯一一处建筑遗存,一条东西走向的窑洞,我们将它完整保留,并作为了整栋建筑设计展开的依据,进而设计成了接待中心的主入口。

接待中心主入口
窑孔处破败的门窗被替换,但传统的窗棂样式被刻意保留,作为一种对于原有建筑在位置上的暗示。帆棚下的阴影成为了访客进入室内前的过渡。客人进入建筑后则直面一池镜面水,上部的天窗同室内连续的拱廊所形成的光影同室外帆棚下的灰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强化了客人对于项目的第一印象。

进入建筑后直面一池镜面水
水池的东侧是一个开放式的售卖区域,里面展陈了一些当地的物产。西侧则是办理入住的吧台,旁边有舒适的沙发区可以休息,休息区自然围合水池形成了一个咖啡厅。
从咖啡厅可以顺势进入位于建筑西侧的餐厅开放区,开放区的一侧直面室外景观,另一侧则可以出到一个室外平台。一个小的种植区将平台和接待中心入口处的灰空间分隔开,为这个平台提供了恰当的私密性。入口灰空间的南侧有一个更大面积的种植院落,U 型建筑南翼的功能空间都围绕这个院落展开布置。
院落东侧的多功能厅可以举办各种活动,高台土崖一侧的独立入口前厅耸立于崖边,立面上大跨度的砖拱以及下方外凸的圆弧体量一并形成了项目的视觉焦点。院落西侧则配合南边微微隆起的土坡在一层安排了两个包间以及儿童游戏区。整个南翼的二层则是多个工坊空间,从这里向南可以越过土坡看到绵延的山脉和沟壑。

东侧凸出的多功能厅入口与下方的老窑洞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整个建筑的南立面是一串连续的拱券,配合室外看景设置的阳台所产生的阴影使得整个建筑立面节奏变得更加丰富。
一层中心部分的开洞使得自然风可以通过庭院穿至建筑入口处以及餐厅的室外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客人的体验。卫生间以及厨房等后勤空间结合场地中原有的护墙被安排在了整栋建筑的北侧,单独设置的出入口及杂物院有效避免了流线上的交叉。
民宿的住宿部分还是保持了隐居乡里一贯坚持的独立院落模式,散落于阳坡村的各处。为了和村落的整体风貌相协调,建筑的体量,外观造型和色彩上都尽量配合旁边的传统窑洞住宅。立面开孔的尺寸,外墙砖的土黄色都尽量同周边的建筑一致。除了少量的窑洞是挖在垂直的崖壁上,村民原有的房屋大多数还是建立在相对平整的土台上,上方的房屋随地势向后方退让,下方房屋的屋顶自然成为了上方住户的活动平台。

独立院落住宿单元鸟瞰
由于是独立建造,这些房屋其实在结构上并不需要采用拱券的形式,但窑孔的造型已经超越了纯功能的意义,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但崖壁上开凿出的窑洞大多是砖石结构砌筑出的拱券,年久失修后大多已有破损,土台上搭建的很多房屋也存在各种安全隐患,拆除后新建反而更加节省成本,空间布局上也更加便于操作。传统窑洞除了作为一种在地化的符号,也因为孔窑上方厚厚的覆土,使得里面的居住空间冬暖夏凉。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唯一的窑孔开口使得内部空间的采光和通风都很差,为了保持内部空间的私密,室内空间无法对景观开放,度假体验很差。由于结构上的限制,窑孔之间被厚墙分隔,即使联通也只能是很小的开洞,导致一排窑洞只能是相互独立的狭小空间。作为新建的窑洞度假空间,为了克服上面所述的问题,我们采用了有更大空间灵活度的混凝土框架结构,拱券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在地化的符号被在形式上保留了下来。
作为最有在地化特征的空间符号,为了保持室内拱顶的完整,所有的灯具都布置在了两孔之间的吊顶里。白天,日光从两孔之间相隔部分上空的天窗经过吊顶上空竖壁的多次反射后从狭缝里漫射到拱顶,含蓄的衬托出拱顶的纯粹。晚间,吊顶上部的线性照明经过拱顶的漫反射后使得室内空间更加柔和温馨。

为了保持室内拱顶的完整,所有的灯具都布置在了两孔之间的吊顶里
独立建造的窑洞民居和土坎之间形成的部分设置了后院。卫生间这样需要更大隐私的功能被安排在了窑洞的最深处,后院的设置使得原本在传统窑洞中黑暗封闭的空间可以开窗采光通风,整个卧室空间的居住体验也被大大改善。由于是混凝土框架结构,屋顶的荷载不再依靠拱券部分的支撑,在客厅部分,相邻窑孔间可以自由联通成为更大的空间,两侧的落地玻璃将室外的景色与室内空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让我们新建的窑洞民居更有辨识度,我们只是保留了窑孔开洞的尺寸,在形式上做了一定的提炼和简化,使得开窗部分能够具有更好的采光性和避雨作用,立面空间也可以更有层次,窑拱部分引入的新材料也使得与周边黄土浑然一色的建筑主体多了一些变化。

窑拱部分引入的新材料也使得与周边黄土浑然一色的建筑主体多了一些变化
除此之外,每个建筑单体都象传统的单体窑洞民居一样,是简单纯粹的长方体,没有过多的变化。多个长方体体量依据周边环境组合形成了不同的院落空间。不同于南方山水的秀美,这样单纯而有体积感的构筑物很容易和周边苍劲深远的环境共生,所有从这万千沟壑中生长出的生命都是如此,从文化到建筑。少了很多精微处的纠结,多了一份坚韧和大度。

多个长方体体量依据周边环境组合形成了不同的院落空间
有别于其他的独院窑洞,15 号院是相对特殊的存在。它位于整个项目的核心,建造场地北侧的土崖让它两层高的体量可以隐在村道之下,南侧却又毫无遮挡的开放向了壮丽的景色。

15 号院位于整个项目的核心,建造场地北侧的土崖让它两层高的体量可以隐在村道之下
整栋建筑共有9 间客房和多个公区,虽然也设有独立厨房,但正如前面产品定位中所提到的,处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在配置上更接近于一个小型的客栈。为了安全,整栋建筑从南侧崖坎向后退了近10 米。
一道沿着南侧崖坎建造的弧墙限定出了客栈的前院,一个相对开放却又和建筑主体产生着紧密关系的活动场地。客人可以从两侧蜿蜒的山道进入,也可以沿着弧墙一侧的台阶拾级而下,到达下方更加开阔的砾石花园。

客人可以从两侧蜿蜒的山道进入
建筑东南角的入口是进入客栈内院的入口。内院是一个由南北两个二层的建筑体量,西侧的单层客房以及东侧的后勤空间共同围合成的空间,它为功能空间提供了必要的采光通风,也为居住的客人提供了一个更加私密的公共活动场地。

15 号院内部庭院
南侧的二层建筑体量中首层是多功能活动空间,既有可供客人灵活使用的长桌,也有专门的茶席和儿童活动区域。

多功能活动空间

茶席
天气好的时候,里面的活动可以灵活延展到南侧的前院。为了配合南侧更加优质的景观条件,二楼部分在东西两侧各布置了一间带有独立起居空间的高标准卧室,以期给运营方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北侧的二层体量中,上下两层各布置有两个卧室,虽然没有南侧二楼上的卧室那样的景观条件,但两个卧室间也设置了公共活动区域,可以进行小型的临时性会议。南侧的阳台可以直接通往东侧后勤用房上面的屋顶平台。屋顶平台周边被枣树包围,在一层庭院被景观种植占用的前提下,为整个客栈留出了一个相对私密的室外活动场地。
乡村改造设计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土地与人的真实联结。从2015年深秋落成的山楂小院1号院,到如今300多个乡村院落的生根发芽,八年的实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朴素的真理:乡村需要的不是建筑师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而是能与土地共呼吸、与村民共命运的可持续系统。真正的评判标准不在图纸上,而在田野间——‘造血功能’决定了项目能否存活,每一块砖瓦的成本必须转化为未来收益的潜力;村民的双手与笑容是最诚实的答卷,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能否从中增收,远比奖项更有说服力;而设计者更需要以“主人”的姿态扛起全周期责任,从建造到运营的每个环节,都要直面市场的拷问:这个设计是否降低了营销难度?是否控制了运营成本?是否让乡村真正“活”了起来?就像田间的庄稼,经得起风雨的才能结出果实,虚浮的幻想终会被土地淘汰。乡村改造的本质,终究是一场褪去光环的修行——唯有让设计俯下身来,倾听土地的心跳,才能让那些砖瓦院落,真正长成滋养乡村的根系。
相关推荐

首页

项目

搜索

品牌

我的

